|
如果你認為3D打印還僅僅是個用作制作原型的酷感技術,請等等,再想想看,這一切是否在發生變化?目前,大約31.4%的中國原型制造企業在使用3D打印技術,而2014僅占21%。值得一提的是國內約6.6%的3D打印是用來制造最終產品而不是原型。
世界范圍內來看,根據Wholers 2016的報告,3D打印2015年的年復合增長率為25.9%,而其中用于生產最終成品零件的比例占到了51.3%,這之前在2014年用于生產的比例是42.6%,所以說用于生產目的的3D打印正在占據主要位置。麥肯錫曾經預測,3D打印在應用端市場的影響力是深遠的,預計到2025年,3D打印對經濟的直接影響是5.5千億美金的規模,這其中包括消費類應用、模具與夾具、醫療植入物及牙科產品、航空航天零件、汽車及其他工業領域。雖然中國的3D打印應用于生產的比例還遠不如世界水平,但考慮到中國是世界生產中心的地位,3D科學谷認為這一現象將發生改變。
作為正在來臨的工業革命,3D打印在制造中所占據的位置在提升,這一現象從全球范圍內來看是明顯的。包括惠普全球裁員將戰略中心“押寶”到3D打印業務板塊上,可以說一切的跡象都在表明,3D打印時代正在到來,開始“擾亂”萬億制造業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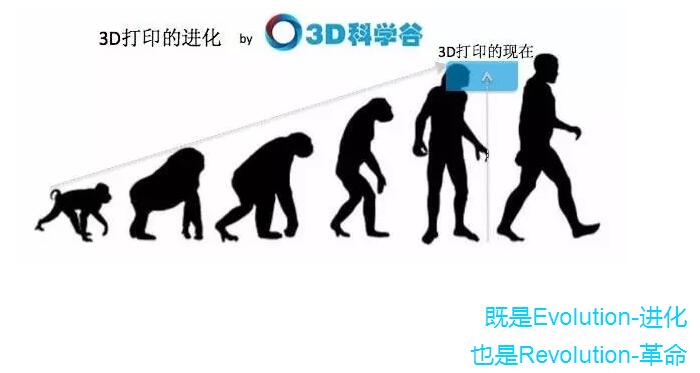
除了惠普,就拿汽車行業的寶馬來說,從2012年,寶馬開始為勞斯萊斯幻影生產零部件,這比GE廣為人知的LEAP發動機引擎噴油嘴還早。這些零部件包括塑料支架的危險警告燈、中心鎖按鈕、電子停車制動器和插座。在寶馬位于慕尼黑的研究和創新中心有一個快速技術中心的團隊(FIZ)。他們每年生產近25,000個原型,還生產近100,000多個零件。零件包括小型塑料載體到設計樣品和用于功能測試的底盤組件。而勞斯萊斯幻影系列準備年生產10,000多個汽車零部件。
醫療行業,強生公司已與惠普、Carbon3D、3D Systems、Organovo及Materialise等公司進行3D打印醫療器械領域的合作。強生子公司DePuy Synthes 還推出了TRUMATCH產品線,產品包括定制化的顱頜面(CMF)外科植入物和手術導板,以及膝關節手術導板。強生的各種努力已經證明3D打印在骨科、眼睛健康以及消費類醫療產品領域都將帶來制造方面革命性的變化。
當然除了這些,像GE、波音、空客在3D打印進入產業化領域的進展就更具說服力了,3D科學谷在此不一一復述。而軟件公司像SAP與物流公司UPS的合作,在美國打造一個按需3D打印的服務網絡。以及SAP與空中客車的子公司APWorks在3D打印相關的協同創新方面的軟件開發合作。這些都使得3D打印在系統化的管理方式上納入到生產的一部分。
其實在3D科學谷看來,不僅僅是GE14億美金收購兩家金屬3D打印企業為3D打印行業打上了里程碑的烙印,也不僅僅是Carbon為首的材料企業將樹脂材料的性能從原型用途推進生產領域。3D打印將要帶來工業革命最直接、具有說服力的信號是全球科技公司西門子將推出一個新的終端到終端的增材制造軟件包,覆蓋設計、仿真和生產的解決方案,這個產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解決方案將從2017年1月開始商業化。無疑增材制造設備要想不停留在單機運作的狀態,而是徹底融入到制造的環節中。PLM對于工廠的運轉就像人體的脈絡一樣,提供一體化設計、全套仿真、數字制造、數據和過程管理。消除了應用程序或過程之間的轉換或翻譯的需要,并將使得汽車、航空航天和醫療設備行業大大受益。
為什么是現在?3D打印技術存在很長時間了,而且我們總是覺得3D打印存在著材料、價格、速度、精度、產品一致性等等各種各樣的問題,究竟是哪些因素匯集到一起催化3D打印的全部潛能?
其實,3D科學谷認為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一下3D打印行業,設備是否還像原來那么笨拙?材料是不是還是那么中看不中用?應用解決方案是否還停留在小打小鬧的階段?
的確,上面的這副圖片現在來看已經OUT了,3D打印已經不僅僅能滿足基本的制造需求。事實是當前的不少設備已經真正意義上進入到工業級別的應用領域的,速度比原來快很多,精度可以匹敵注塑件,最重要的是3D打印邊際成本對產品的復雜性不敏感,況且還有類似于惠普這樣的設備用于多材料的打印,塑料也可以導電,這為產品的重塑帶來了巨大的想像空間,我們可以預見不久的將來,很多產品“長”的樣子將與當前的產品大不相同,圍繞著產品功能的訴求,產品設計不再被制造方式所壓抑,為增材制造而設計將成為common sense。
除此之外,3D打印進入萬億的制造業市場的驅動因素還有更多,即便是拋開背后的經濟效益不談,單是環境與社會效益也是大勢所趨。我們當前用一種堪稱奢侈的方式消費著地球的資源,破壞著賴以生存的環境。我們日常購買的很多產品是從不遠萬里的地球的另外一端運輸過來的,這樣的模式能持續多久?恐怕這也是艾隆馬克思移民火星的計劃廣受歡迎的一大原因。3D打印帶來的即時生產、避免庫存、減少生產計劃不準確帶來的浪費、縮短供應鏈與物流成本為資源的可持續性帶來積極的意義。
更何況隨著全球對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智能制造的重視,除了3D打印又有哪種制造技術天生就帶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智能制造的全部基因呢?
就拿物聯網來說,物聯網和3D打印的結合是雙向的,一個方向是3D打印技術所制造的植入式感應器等監測設備直接“預埋”到產品中作為一種制造技術手段與物聯網發生直接聯系;另一個方向是物聯網所積聚的大量大數據反饋給3D打印的制造系統,以實現更精益的生產及供應鏈管理和更加適合用戶需求的產品設計。
而拿大數據來說,3D打印從模型的建模,到生產工藝、加工參數、仿真、材料性能、產品質量、供應鏈可以說產生了海量的數據。美國早先就以強大數據庫深度布局增材制造,Senvol數據庫就像是一個增材制造行業的Google, 包含了工業增材制造設備和材料的數據。用戶可以在上面根據自己的需求搜索與之相關的信息。其強大的專有算法可以幫助生產者確定哪些部分使用增材制造(AM)會比傳統工藝更加有效。這個算法分析了整個供應鏈,并考慮了諸如庫存、停機時間和運輸等各項因素。
美國國防部先進研究項目局(DARPA)的Open Manufacturing開放制造計劃目的是通過數據來了解制造。DARPA指出,為了使3D打印成為復雜軍工部件——比如飛機機翼——制造的主流技術,就需要對“基于不同屬性和性能材料的各種制造方法所產生的細微差別”有深入的了解。由于無法對3D打印出來的每一個部件都進行測試,目前能做的是對某一個特定的生產批次中的極少數產品進行測試,然后由抽樣測試的產品質量代表整個生產批次的質量。這就是為什么DARPA的開放式制造項目對于增材制造的未來如此重要的原因:因為對于技術和材料的透徹了解能夠幫助公司節省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除了Open Manufacturing這樣聽起來“高大上”的計劃,國際上還有大批針對增材制造進行實時監控及仿真的軟件產品。典型的包括實時監控領域的Sigma Labs,仿真領域的Altair,以及創業型公司Amphyon和3DSim。通過仿真來管理3D打印預期也成為業界共識,而優秀仿真水平的實現正是基于加工中的大數據。
人工智能方面,不僅僅是通過3D打印產生了大量的可用于人工智能領域的產品和零件,包括哈佛大學的軟體機器人。人工智能對3D打印技術也是一個正向的促進作用,這其中就有在線人體模型建模平臺Body Labs。Body Labs的創始人,來自布朗大學的計算機視覺課程教授Michael Black通過機器學習算法來研究成千上萬的3D掃描的真實生活的人在各種姿勢下的人體形狀,并創建了統計模型,這項研究持續了十年,才誕生了Body labs。
而自動化與智能制造方面,3D Systems推出了3D打印自動化式流水線,Stratasys通過機器人實現的“infintely build”(無限制造)。帶機器手的3D打印還包括MX3D、Thermwood、Branch Technology、LittleArm 和 Arevo Labs。 而LENS技術領域,包括博世力士樂與挪威鈦的合作,大隈與RPM打造的Fastems柔性制造系統等等。
另外,除了自動化的機器手可以直接用于3D打印,以及自動化可以將3D打印設備與傳統制造設備相互連接,3D打印還可以貢獻與自動化,這其中就包括自動化供應商柯馬通過3D打印優化夾緊裝置的設計,以及Materialise為ABB優化的柔性機器手設計。
|

